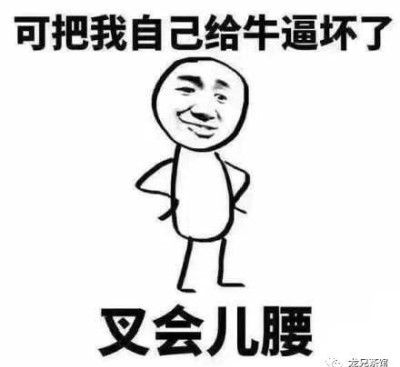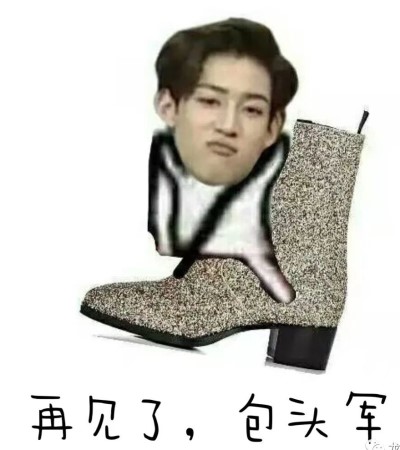儿 时 的 空 气 鞋---------陈辉龙(泉州)高中87届【校友文萃】
|
儿 时 的 空 气 鞋 鞋鞋鞋,曲洞向天歌。红皮不怕水,赤身善爬坡。
在我老家,拖鞋不叫拖鞋,叫浅拖;凉鞋不叫凉鞋,叫空气鞋。 小时候,常听父亲唠叨:这辈子到底是穿草鞋,还是穿皮鞋,就看你要不要好好读书啦。那会儿,我就隐隐觉得,这鞋子好像不只是用来穿的,可能跟身份还扯上关系了。 六七十年代,家里是真穷,记忆中有大半年时间(夏秋季节)都在打赤脚或穿“人字拖”,感觉并没什么不妥,挺惬意的。后来,上了学,打赤脚人家会笑话“阿泥巴巴”,穿“人字拖”老师会说“路鳗田鳝”,小孩子都爱面子,当然就不会再“趁趁彩彩”了。天一热,看见有钱的男同学都在流行一款猪肝色、绰号“包头军”的塑料空气鞋,走起路来是“三脚花跳”,牛逼的不行。输人不输阵,于是,死缠着母亲也买了一双。
咱也有空气鞋了!您千万甭小看它,先来听听这么一个顺口溜:“一皮二球三空气,其他统统在其次。有钱没钱一回事,穿上都是好同志。”它能高居鞋界三甲,足见当年孩子们对它的喜爱。不过,喜爱归喜爱,我自是不会忘了要省着穿,就怕它容易变旧或坏掉,妈妈可下了指示:至少要穿一年!得留待做客或上学等关键时间才可牛逼它一下。 牛逼往往是需要代价的。这“包头军”,包头包尾的,前面不露脚趾,后面不露脚后跟,只有脚库上面是镂空的(最显著的是六个对称的长圆孔)。瞧着没毛病,关键是头尾两边的包块硬巴巴的,很容易磕脚,尤其是新鞋。我刚穿上还不到一天时间,脚趾头就硌得慌,又麻又胀,尤其是那脚后跟,表皮被生生蹭掉一层,渗出微微血痕,刀割似的,走路都得踮蹑着,蓝瘦香菇啊!后头,我向同学们学了一招,拿风湿膏把大脚趾裹实,将脚后跟贴厚,立马好上许多,呵呵,总算可以继续牛逼了。
农村的孩子比较贼皮贼肉,没多长时间,也就顺脚了。这时候,它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下雨时,穿着它净往水堆里蹚,看到那些穿皮鞋布鞋的家伙左跳右闪的狼狈相,乐得嘴巴像个八字;走路时,有小沙石跑进鞋里面,不用脱不用伸爪去掏,侧个脚荡荡地就得了,很是潇洒;偷水果时,可以拿它当掷物,重量轻,面积大,准头足,方便又实用;打架时,绝对是上好的武器,够威够力,一脚踢过去,对方不是乌青就是积血,叫娘都来不及;心花开时,取上鞋来,把鞋底下的石砾或泥土块儿磕出,用糖果纸包好,偷偷放进小芳同学的书包里......不过,我总认为,它最大的好处还是:不臭气熏天不患香港脚!
记得有一回,天气有点闷,上课就把空气鞋脱了,并打起了小盹儿。等我醒来想穿的时候,竟然不见了!临近下课,老师从课桌下抓出一双鞋,可不就是我的!你以为我是坐第一桌吗?我是坐最后一桌的好不好,前面那帮家伙,一脚一脚生生的把我的鞋,从最后面传到老师脚下。天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才能让他们做出这样无聊的事情!但往往无聊可以造就经典,现每每谈及此事,同学们是眉飞色舞,并提议建群名曰“空气鞋之恋”。 虽然是爱护有加,但这空气鞋毕竟是塑料做的,穿一段时间,上边的胶襻就会慢慢开裂甚至断了。不过,同学们个个都是修鞋高手,从工具箱里找一截钢锯条,伸进燃烧着的煤球孔里,几分钟后,用破布包裹住钢锯条外边的一头,快速拔出来,把炙红的那一头小心地摁到断裂处,随着“噗嗤、噗嗤”的声音,一股浓浓的焦臭味弥漫了整个灶脚。空气鞋的断裂处被烫成了稠糊涂,这时迅速拔掉钢锯条,用食指和拇指紧捏接口,稍驻片刻,放开,轻呼一口气,断裂的胶襻就重新粘在一块了。
有时情况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断裂的胶襻多补几次,长度明显不够了。这时,就得从别的废弃的空气鞋上剪下一块儿,当作搭桥,再用烧红的钢锯条将搭桥和断裂处两端分别粘接起来。这个难度系数会大点,有的哥们不小心手就会被熔化的胶滴粘到,甩了半天没甩掉,那一个才叫烫,痛得直用口水涂抺(口水可以消肿止痛,一般人我不告诉他)。接完后,会磕碜点,没关系,继续穿,乌龟笑鳖爬——彼此彼此。 到了最后,空气鞋已经是搭桥复搭桥,真的没法再搭补了,索性把脚后半部分的胶襻全剪掉,变成了“浅拖”。自然,这“浅拖”是不宜再拖到学校,但这会儿冬天也快到了,就让它呆在家里“吧答吧答”,把短暂而又漫长的夏秋拖完吧。 终于有一天,来了一个“敲当当”的,我用它换来了一块“糖甲”,乍一看,这“糖甲”的颜色跟它一样样的。待津津有味吃完那“糖甲”,空气鞋已走了,随“敲当当”的走了,只剩下几道白色的镂迹印在我黑黑的脚背上,似乎在诉说它心中的不舍。 儿时的空气鞋呀,质量虽不好,却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今天的空气鞋谁又会穿破呢?儿时的欢笑也就成了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