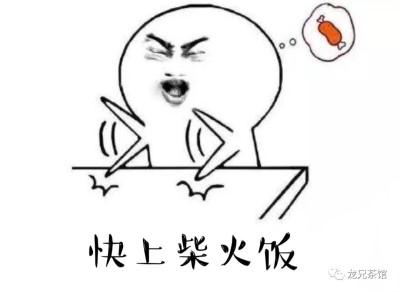难 忘 柴 火 灶------------陈辉龙(泉州)高中87届【校友文萃】
|
难 忘 柴 火 灶 土灶劈柴大锅饭,添碟卤肉拍个蒜。若是再斟二两酒,给个神仙也不换。
前些日子,我在街上闲逛,无意当中看见一家小饭馆赫然写着“柴火灶饭”四个大字,这才发觉很有些年头没有吃上柴火灶做的饭菜了,嘴里开始泛起口水,思绪一下子回到那袅袅炊烟的岁月。 不曾远去,记忆如昨。 开始记事的时候,我家刚从古大厝搬出来,新家是五房看厅的传统样式,为了多腾出一间房,便在左侧多搭了一间土坯房当灶脚(厨房)。灶脚的主角当然是柴火灶了,垒灶前,父亲喊来了风水先生,只见风水先生煞有其事地踱上几圈,尔后拿出一个圆圆的叫什么罗盘的东西捣鼓了一阵子,神叨几句“坐北朝南随屋向,通风靠墙不对门。朝天烟囱台角站,落地水缸锅边。”等之类的术语, 按照五行易理标下具体方位,并帮忙择出了建灶的黄道吉日。“破土”之日,母亲先摆副“三牲”烧点纸钱祭拜灶王爷,禀告一声,祈求“旺火旺气旺子孙、顺鼎顺灶顺透透”。诚心之后,泥土师傅这才根据风水方位和尺寸大小垒起灶来。
你甭说,一个小小的灶台,泥土师傅也是忙活两天才垒好。新修好的灶台真是漂亮!两个放锅的位置,前面一个大锅专用于煮饭炒菜,后面一个较小的锅(我们称之为“后尾鼎”)平常放点水,煮食时,里头的水就跟着热了,可以用来洗脸洗碗等等,很是合理。暖心的师傅还在添柴口和锅上方的墙壁各开了一小一大的两个四方形洞口,小的用来放火柴,大的用来搁油盐酱醋,触手可及,非常方便。灶口的标配也全乎了,小仓凳、火钳子和吹火筒各就各位。整个柴火灶灶面贴上了雪白的瓷砖,在黑乎乎的屋子映衬下,更显得洁白干净。还有那烟囱也十分漂亮,一个个枣红色的瓷筒镶嵌着,斑竹似的,顺着墙壁从后灶台一直爬到屋顶、探出屋外。听大人说,它重要呢,专司拔火拔烟,排走废气,一旦堵塞,得赶紧搅烟囱,否则就会反火呛烟。我记得很清楚,当年用来搅烟囱是一根类似于钓鱼竿的家伙,只不过那“钓钩”换成一个小沙袋了。
灶脚,永远是最诱人而又充满乐趣的地方。 每次做饭的时候,我就喜欢蹲守在灶口,你们不要认为我勤快,错!我才懒得当那“火头军”呢,我的目的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用母亲的说法叫“嘴头紧”。例如:每次焖红烧肉的时候,妈妈总会夹上一两块让我先“试试咸淡”;家里来客人时,需煮上点心,待给客人盛完后,锅底的当然就归我了;有会儿炖个鸡啊鸭啊,一半时间就可以把米料(鸡血或鸭血拌面线)偷捞上一块享用,到最后分汤肉时,还可以先抢上一个正腿(翅膀部分为副腿);蒸龟蒸粿时,一开笼屉盖,立马就可以大快朵颐还带着烟水的龟粿,那一个才叫香;就是平常时煮米饭或麦糊,也能等来几大块噶嘣脆的锅巴......每当我开心地“祭龙喉”时,家里的大黄狗总是吐着舌头,围着我摇头摆尾点头哈腰,我总会扔一小点给它,好歹它也算是我忠实的蹲友了。
我蹲守灶口的另一个目的是:烤地瓜。把一个半大的地瓜埋进灶膛的火灰堆里闷烧,估摸差不多了,掏出来捏捏,如果它浑身已经变得柔软了,那肯定是熟了。滚烫的地瓜在我手里跳跃着,灰尘掸去得差不多时,用手轻轻掰开,里面冒着热气,一股清甜的香味扑鼻而来,忍不住塞进嘴里,结果烫得舌头直打哆嗦,而残留的烟灰把嘴边沾个黑乎乎的,害得母亲在一边直嗔骂:“重呷夭秀”。有时候,我还会把黄豆、豌豆、花生,甚至是啊咦(蝉)或蚂蚱等放进灶膛里烧烤,呼着嘴嗑巴着。说实在的,那些个味呀才是心底最真切的童年,早已渗入到了我的血管,历久弥香,珍贵无比。 柴火灶是母亲的天地,一年四季,母亲忙完田里的活,就在那柴火灶里继续忙碌着。她用她那双灵巧的手,奏响锅碗瓢盆,吟唱油盐柴米,从艰难清贫中蒸煮出飘香四溢、温暖亲切的日子来,满满的柴火味,满满的母亲味道。 父亲这个“大厨”平时是不轻易下厨的,只有普渡、佛生日或过年时,才会“屈驾”亮它一手。这会儿,自然是他主勺,母亲则“退居二线”,当个“伙计”,坐在灶口前,负责生火。但见父亲切炒煎炸蒸,灶前灶后忙个不停,嘴里叼着香烟,还兀自嚷嚷让母亲烧大火或小点火,很有点大厨的范儿,母亲默契地配合着,一道道美味相继而出......那时候,看到父母一道有说有笑地做饭,心里总感到有一种别样的幸福和心安。
我最喜欢看的,是烟囱里冒出的炊烟。 清晨,炊烟像一支棒棒冰,透过薄雾,载着生活的气息缓缓升起,空气中都有了饭菜的香味,似乎在提醒爱睡懒觉的孩子:“快起床,吃完饭后好上学”;如果是在中午,冒出的烟柱直向天空,像一根大麻花,气势磅礴,而后俯瞰着大地,似乎在迫不急待地想告诉我们:“快点儿,家里煮了你爱吃的”;而到了傍晚,炊烟显得非常柔情,扭扭捏捏地钻出囱口,像一团棉花糖,在屋顶上依依不舍地飘曳、盘旋,似乎在召唤着贪玩的小伙伴:“快回家,你妈喊你吃饭了”。直待家家户户亮起灯后,它才慢慢地散开,融入夜色,整个村子就氤氲在朦朦胧胧里。闽南“四句”赞曰:高高低低真好看,心心念念叫吃饭。一年到头不曾断,道是人间最模范。 说出来还有点不好意思,做为一名资深的“灶脚虫”,每每放学后,远远的我就可以通过炊烟判断家里的柴火灶煮的是什么。如果炊烟清淡疏朗,那一定是在煮稀饭或麦糊,稻草、麦秆或蔗叶小火烧的;如果炊烟是急促夹火,很有可能就是在爆炒什么好料,山芒、树叶或松针猛火催的;而炊烟若是黑烟滚滚,大概率是在炖猪脚或鸡鸭,柴块、干枝或树蔸硬火焖的。炊烟,就是吃饭的号角!眼珠子在眺,脑瓜子在想,哈喇子在流,脚丫子在跑,正所谓:日照烟囱生紫烟,遥看口水挂嘴边。吸溜一下两三尺,疑是猪脚舞蹁跹。 我每每觉得,那袅袅的炊烟里满是最平常的人间况味,朴素、温暖而芳香。它就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塔,守着它的是母亲的爱,盼着它的是儿女的情。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渐行渐远的流年,再也见不到那流连的柴火灶了,再也见不到那迷人的炊烟了。这次,“柴火灶饭”重现江湖,得空一定得跑去品尝一下,寻找那遗失的味道,不知有哪位哥们姐们愿意一道去,听说还有土猪肉、大肠羹,我请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