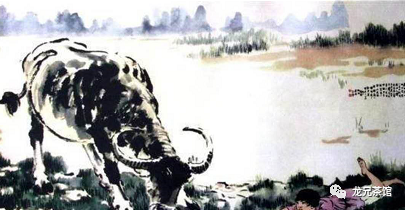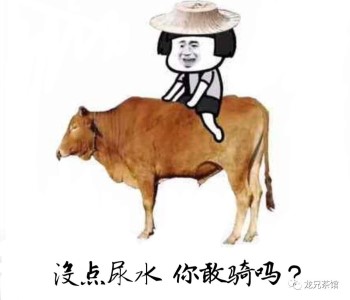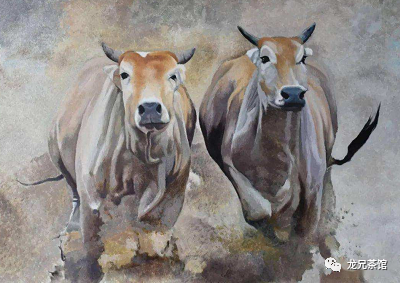放 牛---------------------陈辉龙(泉州)高中87届【校友文萃】
|
放 牛 放牛日当午,山坡烤红薯。穿着开裆裤,跳起芭蕾舞。
一提起“放牛”这个事儿,你也许会想那万恶的旧社会,其实并没那么远,只要是六七年代农村出生的人,基本上都干过这号事,当过牛倌儿。 七十年代末,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牛也随着土地分配下去,每四户人家一头牛,这样,牛就没办法再统一放养了,黑番的媳妇梦也就此破灭。经过集体讨论,最终结果是每头牛由其归属的人家轮流各放养一周。于是,每逢周末,或者是暑假(冬天牛一般吃干草),放牛这差事,便自然落到我们这些十来岁孩子的身上。
记得那会儿老师和家长经常吓唬说:“不好好读书,就回家去放牛”。他们哪知道,在当年,这放牛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件美差!因为,那时候,承包责任制刚实行,家里的大人整天忙里忙外,永远都有忙不完的活,节假日里,经常会违反纪律使唤我们这些童工干这干那,比如养鸡养鸭挑水挑粪,比如煮饭扫地割草喂猪等等,干不好还要给个脸色或数落几声,烦的要死,倒不如去放牛,不用费什么劲儿,还落个耳根清净,当然,最最重要的,是有得玩! 马怕满天星,牛怕肚底冰,据说牛不能吃带露水的青草,否则就会拉稀,所以,可以一直睡到太阳照到屁股,哥几个才相互招呼着到牛圈里牵出各自的牛儿,浩浩荡荡的来到生产队后边的山头上,各自寻上一块合适的草地,把牛鼻绳放至最长,绑在牛坎上,之后任由它们在圈定范围内吃草。正事办完后,大伙便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地聚在山坡上打闹嬉戏,编柳条帽抓坏蛋,抓住后捆在树上“拷问”;玩捉迷藏,藏在树坑里,猫在草丛中,更有胆大的躲在坟堆后,让其他的孩子不敢接近;偷东西吃,花生、果子用袖口擦擦直接吃,土豆、红薯和玉米就点个火,烤着吃;如若天气实在太热,干脆扒光衣服,溜进山脚的小水沟里凉快凉快......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到了饭点,大伙先消灭一下身上的“罪证”,这才把牛牵回。下午,待太阳没那么毒时,再重新出发,涛声依旧。
有时候,刚好没有放牛的小伙伴,我一般就不去后山了,直接到就近的稻田边,找一条青草多的田埂,牵着牛一路吃,慢慢往前移动。这时你就要小心了,这牛儿鬼精呢,一瞧你不注意,一别头,“涮涮涮”狠卷几下,一小片秧苗就没了,这是会招人骂的。除此之外,你就可以跟牛儿来个亲密的接触。我发现,牛的眼睛除了大以外,里面总好像有水一样的东西在流淌,“水汪汪”的词组形容的应该就是如此吧。还有,我发现牛身上老爱长一种黑色的像瓜子一样的东西,听大人说,那叫“牛蜱”,是牛的一种寄生虫,于是,我总会将它们一个个揪下来,再用脚踩爆,每揪一个,牛儿总会摇一下尾巴,可能是在表示感谢。我还发现,这黄牛是不能骑的,它的表皮很顺滑,很难骑稳,而且好像很不喜欢人家骑它,每次我的腿刚触到牛肚子,它不是尥蹶子,就是回过头来,一犄角把我剜了下来。有一回,它站在水沟里,我站在田埂上,我趁牛不注意,一跨就坐到了牛背上,牛像是受到了惊吓,猛地向前冲。我的脑袋立时一片空白,等我回过神来,人已经是跌在沟里,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动骑牛的念头了......
队里的五头牛,一公四母,平日里都相处得很好,不管是在牛圈里,还是在野外,很少看见它们闹别扭。但很奇怪,它们好像也跟人一样,有排外的思想,只要有别的牛进入它们的警觉圈,它们就会停止进食,竖起耳朵静立戒备,如若是踏上它们的势力范围,它们立马迎头痛击。你别看牛儿平时憨憨的,可一旦发起牛脾气,顶在一块,三岁牯牛十八汉,你一时半会还很难拉得开。另外,那头公牛,我们外号管它叫“老流氓”,平日里是中规中矩,可有些时候会一时性起,突然跳了起来,前两腿趴在某头母牛身上,光天化日之下,欲行不轨。这阵势相当刺激,周围的老少爷们都会凑过来瞧个稀奇,一个个眼睛瞪得牛蛋似的,而户主不知何故总是棒打鸳鸯,又拉又拽又打,好不容易才把这骚货扯下来,好戏没了,大家伙这才失望地散开。
这牛我一放就放到高中。一进入高中,一是人长大了,二是学习任务也比较重,所以放牛都是一个人。我最爱去的地方还是那个后山坡,把牛鼻绳往牛角上一绾,让它自由觅食,而后找个旮旯坐下来,静静看书,时不时瞅一下就行了。说实在的,在那个路不拾遗的年代,牛是不会丟的,关键就是怕它们去祸害庄稼。我自个觉得,在旷野中读书真的别有一番情调,郊外空气负离子含量高,不容易犯困,又没人咶噪,学习效率很高。有时心血来潮,也会对着牛朗诵一首古诗,或者大声读上一段英文,不用担心人家笑话“拿牛棍、读牛书”。这会儿,牛儿总是盯着我,喷上几个响鼻,应该是表示赞扬的意思吧。我至今还非常留恋这段“对牛读书”的历史,没有是是非非,没有生活压力,没有烦恼,没有套路,只关心书不要弄脏了,牛还在不在。 自从上了大学,离开了家乡,我就再也没有放过牛,再也没有见过那五头牛了。不过,我经常会在乡愁中遇见它们,它们或者在乡亲们的吆喝声中进行着耕作,或是在绿草如茵的田野上漫不经心地啃着悠闲,或是在乡村曲曲弯弯的小路上咀嚼着乡音,或是卧在池塘的柳树荫下反刍着光阴。它们仍旧吃着草,睡着牛圈,出着气力,拖着农民的祈盼,在希望的田野上,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奋蹄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