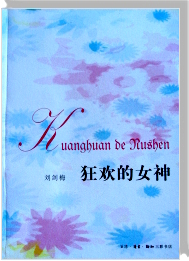倾慕与怀念(第一节)--------郑波光(厦门)高五组【校友文萃】
上传时间: 2007-07-13 【字体:
大 中 小】
|
倾 慕 与 怀 念
——谢刘剑梅刘再复赠书《狂欢的女神》
敬悼怀念刘母叶锦芳太夫人
郑波光(厦门)初20组 高五组
(第一节 倾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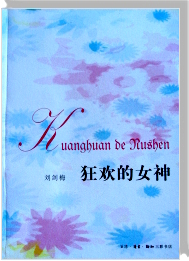 |
|
刘剑梅著作《狂欢的女神》
北京三联书店版的封面
|
2004年8月27日在我工作即将退休的最后半学期开学时,我从中文系我的信箱拿到刘剑梅刘再复从香港寄赠给我的一本书,这本书叫《狂欢的女神》,这本书无论从物理的分量,还是从精神的分量来说,都是很厚重的。香港的书纸质好,印制精良,加上书前四张八面彩页,拿在手上沉甸甸的,看了书的内容,精神上更有沉甸甸之感。刘剑梅在“后记”中给自己的写作定义为“液态写作”、“水上书写”,她这样写道:
“我所定义的‘液态写作’或‘水上书写’寻求的其实就是这种真正属于女性的源泉——女性创造力的源泉。在‘辑一’中,我写了一群独特的女性,有女导演、女作家、女画家等。我写她们,是因为她们的存在方式与创造方式给我带来了激情与灵感。这一群女性像狂欢的女神,勇敢地冲破男性规范的束缚,回到生命的本体中……在种种人生的困境中寻找基本人性的永恒内涵。在我眼里,她们的艺术是一场辉煌的凯旋:不仅成功地回归于真实,也成功地回归于生命的本然。比起她们,被都市物质生活剥离得只剩下空壳的米亚们(“后记”开头就介绍,米亚是女作家朱天文小说《世纪末的华丽》中塑造的一个后现代都市女性,她是女模特,像衣架子,生活在品牌里,最后丧失一切生命本真,变成了一朵空壳一般的乾花。)好像丢了灵魂,如同乾花一样易碎。”(第337-338页)
这段较长的引文,可以作为全书主题的梗概。同时是“狂欢的女神”这个书名的解释。刘剑梅是刘再复同学的长女,我见她时她已上高中,我是在这本书前的“刘剑梅简历”才知道她的简历的。她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现为美国马里兰大学亚州与东欧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我还从她的博士导师在她的新版书《序》中知道:“在去年(大约是2005年)一举得到终身教职。在同辈中,她的际遇应该算是最出色的之一。”
我读过剑梅的一些文章,我觉得她的视野十分宽阔,知识准备相当扎实,心很细。她很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张爱玲曾经说过一句很博大的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八个字原是她说别人的,但人们认为作为她的自我写照更适合,我很赞成)剑梅经历远没有张爱玲那麽丰富,奇怪她居然也接近这种境界。我想这是她心细,又善于设身处地去体察的缘故吧。我觉得,张爱玲深懂女性的弱点,她要拯救女性;刘剑梅体察女性弱点,感悟女性优点,她想帮助女性。一位用作品,一位用理论,都是用心良苦。不同程度都给世人以启迪。书中有一篇文章是研究上世纪现代左翼作家白薇的,《白薇:挣脱身体牢房的左翼女性》,在大陆,很难看到这样深入骨髓、刻骨铭心,又如此人性化的文章。多看的是左顾右盼甚至助纣为虐的宏文。凑巧的是,1985-1992年我住山西太原侯家巷太原师专宿舍,我那楼的二楼住一位已退休的60多岁的老太太黄忱中老师,听她说,白薇是她的姑妈,写此文我查《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二分册白薇词条,她是湖南人,原名黄彰,黄老师就是湖南人,与姑妈同姓,不会有错。黄老师跟我讲,姑妈一直独身,长住北京,有一个保姆,老想骗她钱,但她并不糊涂。一直到我1992年离开太原,白薇似乎还活着,1894-1992,都快百岁了,经历那麽坎坷,生命力如此顽强,真是了不起!以前没研究,从剑梅的文章,我才如此触目惊心地了解白薇的全人,她的男朋友左翼诗人杨骚给她染上性病,弃之不顾,趁她重病,又改写她的日记,掩盖真相。长达900多页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悲剧生涯》,是白薇1925-1935年痛苦爱情的记录。文中写道:
“十年来,她经历了‘爱的春风’、‘革命的春风’、‘文艺勃兴的春风’,但是这三重春风体现在白薇身上却成了‘三重厉雨’、‘三重绝望’。她的身体先是被父亲出卖,然后又被情人出卖,最后又被革命的团体抛弃——所有这些痛苦的身体的经验,让她获得了一种真正属于女性的视角来看待‘五四’以来宣扬的‘个性解放’,”
“然而正是白薇自己残破的身体使得她对‘时代的巨轮’有一种深刻的怀疑。”
剑梅文章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宽厚平和的心态和叙述语态,文章有气势又不咄咄逼人,让人平心静气地听她娓娓叙述,是非感毫不含胡,却毫不激烈。容易让人信服。实际上她也常针砭时弊,颇有见地。试看《为自救而写作》,对“我这一代人”的针砭,可谓一针见血:
“我这一代人,是理想破灭的一代,又是相当自负的一代,因此,既缺少‘救世情结’,又缺乏自救意识。”
很准确,又很有分量。再看她对911后美国的诸多评议,可以确定,剑梅已经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了世界人文知识分子的岗位上了。她的父亲刘再复在《序:亲情与才情的双重诗意》文末写到剑梅的博士生导师王德威教授对他说:“没想到剑梅还很有大将风度。”从我所看到的,从以上点滴引述,剑梅对历史与现实宏观的鸟瞰,以及颇有力度的概括与点评,大体可以印证她的博士导师王德威教授对她的赞誉:剑梅确实颇有大将风彩。
剑梅的成才,刘再复刘剑梅父女亲切的、和谐的精神联系,令我十分的倾慕。
2007年6月1日我又收到《狂欢的女神》大陆北京三联版的著作,这是从《读书》杂志寄来的。这本书与香港版主体内容完全一样,但有所扩展,特别增加了剑梅的博士导师王德威的《序一:女性学者的憧憬》,刘再复原序作为《序二》。夏志清、王德威是我最为景仰的两位海外学者。再复兄的长女刘剑梅能够成为王德威的入室弟子,直接带的博士生,真是太幸运了。真让我羡慕。大陆泛滥成灾的关系学,不可避免地会让人以为是通过父亲的关系,剑梅才会成为王德威的学生,从王德威的《序一》,才得知完全不是这样,“哥大东亚系甄选学生一向严格,剑梅能够脱颖而出,凭的是她在北大以及科罗拉多大学硕士班的专业训炼……直到剑梅入学以后,我才知道她的父亲是刘再复先生——这果然是家学渊源了。”(第7页)这又让我想起再复兄对女儿要求的严格了,当年中国人民大学要免试收取剑梅,是父亲刘再复不准,逼着剑梅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女儿很争气,居然考上了。王德威在序中还讲到了父女精神上的血脉联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影响剑梅创作及问学最重要的源头是位男性,即父亲刘再复先生。展读书中这对父女间的文字来往,有亲情的深深眷恋,也有学问的彼此支援,而我更好奇父亲的影子对我们的‘女神’有多大的影响?”(第10页)确实如此。我注意到,刘再复在对女儿上,有严父的一面,也有慈母的一面:先讲多年前在北京劲松家里,一次再复跟我讲小女儿小莲的一件趣事,再复会写大文章,却不会做家务事,家里常来客人,一张口就称呼再复“老师”,小女儿很奇怪,就问爸爸说:“爸爸,你那麽笨,他们为什麽叫你老师呢?”说完大笑。从中我感受到再复对女儿的慈爱。在大陆版剑梅的《小跋》上,讲到压力很大,“因为父亲对我的期待有时候过高了”,这是严父的一面;但是,这本集子,却是父亲亲自动手,“把我的书房翻个遍,编成了这本集子”(330页),这就是再复慈母的一面了。有这样的父女关系,实在是让人羡慕不已的。
我之所以对老同学如此成功地培养了这样出色的女儿,津津乐道,格外地倾慕,是因为再复兄象一切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全心全意致力培养子女走读书上进之路:学士、硕士、博士。刘再复同学在自己的长女身上完美地实现了。从我内心讲,再复兄有许多成功,但他的一切成功,没有一项大成功,能象培养女儿这一项成功更让我倾慕。
我只有一个儿子,儿子可不象女儿听话。据说王蒙曾说过,儿子与父亲永远是对立的。王蒙说的很可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儿子并不笨,很小就表现有趣的语言能力,四五岁他妈妈带他到校办工厂上班,青年工人逗他玩,他也不吃亏:“你再狡滑也没有我聪明!”把所有人都逗乐了。儿子甚至很有思想,就是不爱读书,高中毕业后,成绩自然不理想,自己报考计算机专业,入学后,想到计算机只是工具,自己不愿意当别人的工具,便选择可以自主的文学创作道路。他从小就喜欢科学奥秘,又喜欢文学幻想,毕业后,自己选择的职业是自由撰稿人,主要创作科幻小说。他完全违背我的、象一切知识分子那样的心愿。但我不能阻止他,只有支持他。我注意到,他的科幻小说视野很开阔,原创性强,又很有人文思考。常常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的8000多字短篇小说《哲学连队》,得到作家韩石山的赏识,发表在《山西文学》2004年7期,这是对于人类战争的哲学思考,我完全没有料到,角度独特,手法独特,算是起步。这篇不是科幻小说。现在大陆文学出版、科幻出版,暗道极多,2005年写一部15万字长篇,2006年差不多用一年时间精雕细刻,又写一部21万5千字科幻长篇,我以为很吸引人,我很久都没有读过这样让我放不下的小说,思考和文字都很有味道,但今年初自由投稿出版社,如泥牛入海。我问厦大朋友,答曰“很正常”,一年、两年才有消息,都是正常的。这条路实在艰难。但儿子坚定,并坚持不走关系,要自闯天下。儿子从小,口才不错,阅读挑剔,对名著常有自己独立见解,他极喜欢高行健,这也是我想不到的,大陆许多人读不懂高行健,还有人“批判”高行健,他却高度赞赏高行健。不过他完全不是“粉丝”式的崇拜者,高的优缺点他的心中都有数。每当创作思路干涩,就读《灵山》《一个人的圣经》,高贤兄惠赠我的台湾联经版的高行健的著作,使他受益非浅。他认为,高行健手法很新,极为灵动,再复兄惠赠《高行健论》他很赞赏,认为见解、文字不同凡响。有时与儿子交谈,见他常有奇思妙想,出人意外。我有时自己心想,将来如果成功,也想劝他,功成勇退。有朝一日成名了,有机会被高校聘任,他还是象刘剑梅一样,到高等院校当教授去,更单纯。这是我这个老头子的痴心妄想,儿子是不会听我的。从这点看,还是女儿好,女儿听话。剑梅在“小跋”上用父亲“逼迫”她这样的词,可见有时也不情愿,但是还是听了,做了,因而也成功了。儿子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我这里,父子冲突不计其数,岁月过去,还是父亲妥协。“儿孙自有儿孙福”,只能用这种民间俗话来聊以自慰了。不少朋友,关心我儿子的情况,我顺便写在这里。因此多唠叨了几句。
 |
|
刘再复和穿博士服的女儿刘剑梅
|
这部新版书增加了许多照片,最引我注意的是197页“爸爸与穿博士服的我”,这张照片取代了旧版167页“1992年与父亲刘再复摄于科罗拉多大学毕业典礼上”。我注意的是,在这两帧照片上,再复兄有最快乐、最欣慰的笑容。上边说了,知识分子对子女的最大心愿,是读书上进,我们当年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读书时代,是“革命”得丧失理智的时代,只有本科学历,连“学士”学位都不授予,而再复长女,远远超过:学士,硕士,博士,而且货真价实,是颇高档次上的硕士、博士。想到大陆教育在愚不可及的工科思维的操作下,人文丧尽,教育滑坡,不可以万里计,硕士、博士,名不符实者居多。能在美国获学位,不是更可羡慕、更可欣慰的吗。
|
相关作品